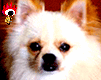外滩记者刘莉芳/报道 小武
“大幕拉开,喜庆的吹打乐声起来……转眼间,只余新娘一人,独自坐在床沿。收光。静了一会,新娘揭开盖头,四下看看,忽地扯下来,四下再看,不解而又害怕地叫道——人——呢?”
这是话剧《金锁记》的序幕,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曹七巧一开幕就掉进豪门深院,大红色调的喜庆下,她的渺小和悲苦被舞台无限放大。和原著从三十年前的月夜开篇相比,话剧受舞台空间和时间等表现形式的限制,它更剧烈地震荡着曹七巧与姜公馆的落差。
这部有电视剧版本在先的话剧,首演依然吸引了众多人气。10月20日晚18:40,上海话剧中心的门口。距离《金锁记》的开场还有50分钟,已有不少人早早地守在门口等退票,而无聊的黄牛因为拿不到票,悻悻地在一边开骂。这种一票难求的局面,在上海话剧界已是久违了的,据制作人李胜英介绍,在首演前,第一轮6场的票就已全部卖完,而现在看来,11月第二轮演出的票房也是一片飙红。“类似这样票房火爆的情况以前也有过,但没这次这么彻底。”上海话剧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则直接说,《金锁记》带来了强大的惊喜。
这种惊喜的制造者正是第一次导演话剧的黄蜀芹、第一次改编话剧剧本的王安忆以及整个创作团队。在和曹七巧纠葛了两年之后,王安忆终于把她甩下。这是写作风格一贯冷静的她的第一部“一反常态”的作品。剧本除了保持原来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构架之外,对白充满戏剧性,剧本虚实之间张扬着戏剧冲突。
黄蜀芹说:“王安忆的剧本没有抄原小说的一句词,但充满了张爱玲原著的精神,台词之间非常有戏剧的张力。其实什么叫张爱玲的语言,我觉得安忆已经做到了这一点,她的剧本中那种冷冷的、很犀利的,但又不是骂大街的那种味道掌握得很好,对小说的取舍很干净。”
这是小说中所没有的,道具和肢体在舞台上也唱足了戏。用黄导的话说,七巧和三爷在舞台上跳“双人舞”,在肢体的舞动、牵引下,彼此的欲望在燃烧。借着道具,那是一只小小宣德炉,或是一把扇子,或是一袭拖地的透明白纱,两人若即若离,欲拒还迎。也是一个道具,一串佛珠、一只手镯,在最后一幕戏中,竟生生地把情绪推往极端。在七巧歇斯底里地破坏了女儿长安的婚事,与姜家所有人撕破脸似地对嘴时,那只镯子恐怖地套在她的胳膊上。
作为主线人物,七巧掌控着全剧的节奏,她从大红镶蓝色亮片的旗袍,到大红描金的旗袍,再到黑色滚边的旗袍,人物在逐渐走向彻底的黑。在这种不可抑制的“沉”下去的情节中,舞台上刻意减少爆发的戏,在嘻嘻哈哈间,七巧与姜家一次次交锋,与女儿正面冲突。这种内敛令情节更有了刻骨的推进,直到七巧的眼神变得凄厉,身躯颤抖,话语刻薄,夹杂着无奈的内心挣扎,手里的佛珠被生生挣断,珠子在舞台上一地乱滚,她也滚在舞台上,哀哀地,黑暗中,一个声音,“人——呢—
—?”
从红色跳到黑色,七巧始终没有逃脱悲的命运。在全剧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,王安忆在曹七巧的一楼,安排了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——以“孩子”这一新力量、新生命的象征,打破剧中沉闷、晦暗的现实生活。这浪漫一笔,让人想起了《日出》最后陈白露死去时,窗外响起的热火朝天的工地打桩声……
与电视剧版不同的是,话剧版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忠实于原著,尽管抽离了长白一条线,但更精练地贴近主题。庆幸舞台给了七巧展现“太多的欲望和热情”的空间,而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和性格,更没有给她一段莫名恋情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话剧《金锁记》不仅仅是张爱玲的,她也是王安忆的。
相关专题:外滩画报